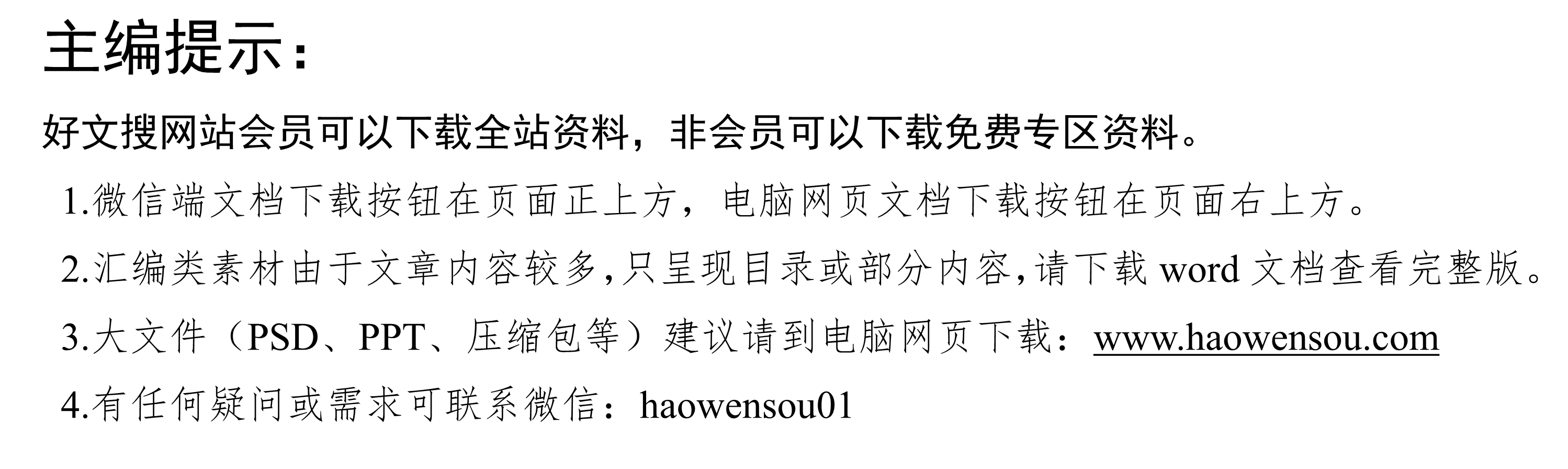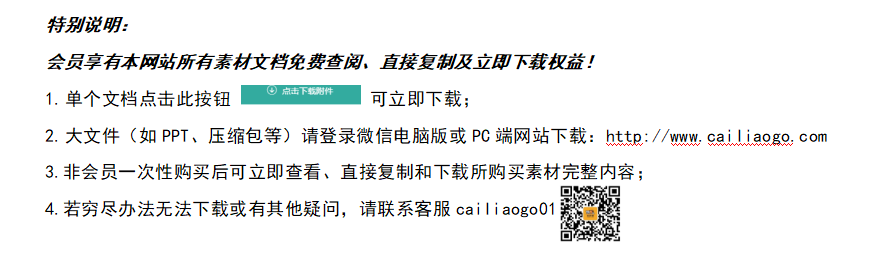党课讲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异化批判、剥削批判和危机批判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之所以成为一种批判性理论,是因为它内蕴着、承载着马克思对正义问题的思考,究其根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正义批判。古尔德曾明言,“在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马克思揭开了其正义理论的伦理实质”。这启示我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是其正义思想的载体,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本质是一种正义批判。进而言之,正是由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关注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剥削现象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危机,才切实地开显出隐藏于资本主义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背后的实质性不正义;也正是由于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本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显现为不同于任何一种传统的整体性、综合性、发展性理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异化批判
在20世纪70年代那场关于“马克思与正义”的讨论中,不少学者将异化视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不正义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对于马克思来说,异化可以成为不正义的内涵?纵观马克思的文本可以发现,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异化批判与其对资本主义制度正义性质的审判之间,并不存在显而易见、不证自明的关联,直接认定“异化即不正义”显然并不合适。故此,我们需要立足于马克思阐发异化问题的理论和现实背景,分析其在文本中对异化问题的具体论述,进而回答“异化何以构成资本主义制度不正义的原因”这个问题。
大体来说,异化是指主客体间的对立状态,即主体产生的客体成为一种支配主体的异己力量。尽管在早年间,马克思也曾谈论过政治异化和人的自我异化问题,但深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之后,异化就具体地指向了劳动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异化不仅仅是“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能力的客观的漠不相干性”,究其根本,异化是资本之于劳动的支配关系,而这一支配关系本身又是劳动自己生产出来的。然而,资本主义当然不会公开上述异化劳动的事实,他们往往以交换过程作为生产过程的掩蔽,以自由平等的交换去掩盖生产领域中异化劳动的事实,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一片平和、繁荣的景象。可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越是发展,异化劳动就越是持续而不可自解,资本主义制度也就越发成为以资本为核心的制度化、系统性的控制模式。
可见,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毋宁说,异化指向的是资本对劳动制度性、结构性、不可自解的支配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制约性。所以,我们可以从“外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两个方面,来理解马克思话语体系中异化与资本主义制度非正义性之间的关系。从外在角度来说,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单向度地支配劳动,劳动无能为力地依赖资本,这种依赖进一步形成拜物教;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拜物教特征,导致它倾向于使历史性的社会关系自然化。根据马克思对社会正义的认定,这种社会关系显然是不正义的。从内在角度来说,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交换领域和生产领域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对自身所有权的根本违背和改变使得它不符合自身早先确立的正义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