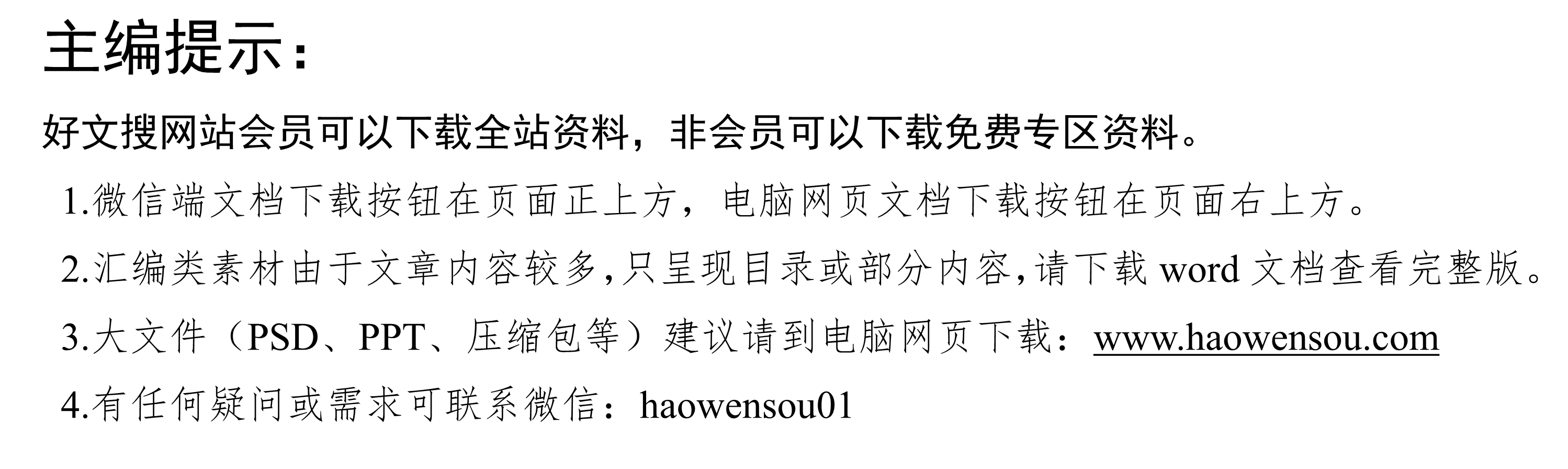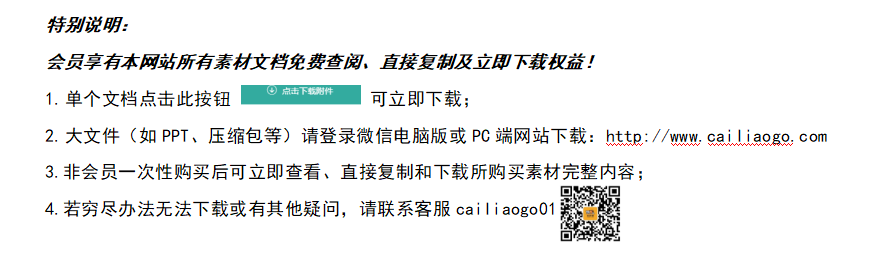在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研究开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最高决策层明确提出谋划新一轮重大改革举措,口风出来以后紧跟着有一句话: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这个逻辑,跟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的几轮大动作,是完全一致的:改革开放初期宏观层面首先动作的,就是在渐进改革、不可能“大爆炸式”这个大前提之下,首先在分配环节的财政实行“分灶吃饭”,作为突破口;到了小平南方谈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之后,他的意识非常明确,必须要有新一轮改革的推进,让xxx在一线主持经济工作,19xx年紧锣密鼓做了准备,19xx年元月一日推出分税制改革,被评价为里程碑式的大手笔。我的愿意特别强调,94年是从分灶吃饭的“行政性分权”,推进到了分税制为基础分级财政的“经济性分权”,为市场经济间接调控机制,和后来中央强调的“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制度安排支撑条件。
在xx届x中全会谋划全面深化改革的“xx条”文件里面,特别明确地说,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最高层级权威的文件第一次如此明确表述财政的重要性。其后,政治局首先审批通过的是财税配套改革方案,后面才是其他方方面面的改革安排,而且当时的时间表上,是说这套改革要于20xx年取得决定性成果,而对于财政方面的要求,则是要提前到20xx年取得决定性成果。后来由于实际的进程并不如愿,官方媒体和官方文件不再提原来的时间表。现在已经明今年x月要开三中全会,财税改革单提出来,显然是放在先行军或突破口的位置上。大家意识到光讲先行和突破,远远不能解决改革深水区的问题了,必须是在有先行的突破选择的同时,至少要有“最小一揽子”的配套设计,中国的改革在渐进改革路径上必是“多轮最小一揽子推进”,一轮一轮代表性的大动作,三中全会以后应有新一轮的部署。不排除这次仍然是解决一部分问题,对真正使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理解,可能方方面面还有不同,要看中央在这次三中全会上怎么样做表述和部署。我个人感觉可能会是强调有力度的一次——最新的政治局会议,对改革前所未有地作个六个方面“必然要求的表述”,强调是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法宝,也就是过去说到的“关键一招”、“最大红利之所在”。作为新质生产力来源的创新,起龙头作用的是制度创新,即实质性地中等化改革,中央这个定位的意义是相当明确的。
落在新的一轮马上要体现在三中全会形成的权威性文件配套改革部落中的财税改革,是今天要讨论的主题。这方面我毕竟做了几十年的研究,我依据一份很浓缩的仅xxxx字出头的简本(是xx前段时间向我的约稿,后来翻译成英文登在报纸上)了。中文表述的主题,就是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方向与思路》,我说说这个框架。
不久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导精神中间,明确给出谋划新一轮重大改革举措和谋划新一轮财税改革,领会这一重要信息,可简单回顾一下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于上世纪70年代末拉开帷幕已来,已经有几轮重大举措,宏观层面都是选择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财政作为先行军展开的,也称为突破口。当下的谋划,要考虑的是纳入整体配套改革,是合乎逻辑地在中国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之上,再次把财税改革提上议事日程靠前位置,单独在中央口风里面点明。财政体制服务全局,改革后总体的取向下是分权取向,从分权取向的变革来看,xx年代分灶吃饭,当时体制内的说法叫“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以后十几年间有些阶段性的调整,其实总体上都是分灶吃饭大概念之下的,比如说两步利改税以后,19xx年曾经说划分税种,根据分级包干来运行,当时所谓划分税种还是按照隶属关系形成的税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税制,还是在分道吃饭的框架运行。
后来里程碑式的19xx年的改革,应该特别强调:它的历史性贡献在于“经济性分权”的框架由此得以建立了,有重大的突破性。实际上,切入点是在中央方面老一辈和当时在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有高度一致的共识,就是中央那样财力非常紧张的状态不能不改变了——以后很多人说19xx年分税制就是正确处理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应说是从这个角度切入以后,作了是全面改革的配套。如果说分税制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正确,但是远非全面,19xx年改革是同时解决三大关系如何三位一体化正确处理:首先应该提到的,还是总书记不断强调的改革核心问题是政府和市场或者政府和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的关系,跟着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还有一条是在现代国家治理里必须单列的公权体系(具体表现为各级政府)和作为自然人的公民、纳税人之间的关系。19xx年体制是三位一体地把正确处理的初步框架确立起来了。下面分别说:
分税制形成框架以后,政企关系是所有的企业不论大小,不看经济性质,不讲隶属关系,不排行政级别,在税法面前一律平等,该交国税依法交国税,该交地方税依法交地方税,税后可分配部分按照产权规范和政策环境企业自主分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终于刷出了所谓各种企业公平竞争的一条起跑线,关键性制度变革的历史意义是非常重要的。由于有了这样一个变革,国有企业从国营改口叫国有后,它还一直存在的行政级别,于19xx年以后合乎逻辑地自然可以淡化(这个还不一定做得特别彻底,但是总体而言是在淡化过程中前所未有的地有了实质性的推进),跟着是跨隶属关系、跨经济性质、跨行政区划的企业兼并重组,在这个环境里开始有了弹性空间。实际运行中19xx年以后,我们看到改革中必然要推进的存量重组开始活跃起来,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要求的充分流动在这方面有了新局面。以后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顺理成章跟着推进,对接现代企业制度的代表性形式股份制。股份制框架下,可以很清晰地将各种所有制主体的持股合在一起,共存共荣共同发展,这个主打的称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企业改革方向,在逻辑上否定了国进民退或者国退民进之争的实质意义,形式上看的谁进谁退,如果纳入混合所有制,要归到大家不是简单的进退的关系,而是共存共荣混在一起共同发展的关系,这个意义当然就非常重大。
小平南方谈话明确了搞市场经济,显然分税制是在市场经济基本资源配置机制方面开了新局,改变了过去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条块分割”地控制企业的格局。分灶吃饭以后,只是从原来的条条为主变成块块为主,政府主体控制企业仍然是按照隶属关系,讲求以“婆婆”意愿能够实质性地去控制’媳妇’的行为,这样一种条块分割、按行政隶属关系组织财政收入和控制企业的旧体制根本弊病,在块块为主情况下,造成了放权让利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企业仍然活不起来的结果。19xx年以后,这个局面终于改观。